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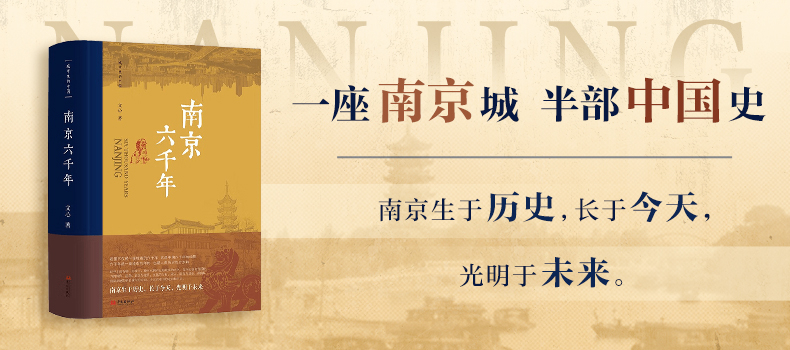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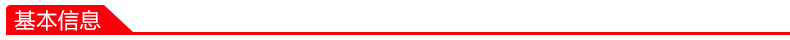
書名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
定價 88.00
出版社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版次 1
出版時間 2017年12月
開本 32開
作者 (英)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
裝幀 精裝
頁數 568
字數 320000
ISBN編碼 9787559610782
重量 505

★我們是誰?我們該怎么做?作為20世紀后半葉ju影響力的思想運動之一,現代存在主義通過回答這兩個問題,在戰后世界的文學、藝術、影視等領域產生了曠日的影響,了解存在主義,就是了解我們想成為怎樣的自己,因為你經歷了什么,那這個什么就是個哲學話題。現在的我們,比我們想象的更需要存在主義者。
★原來你是這樣的薩特、波伏娃、加繆……貝克韋爾以輕松、活潑的筆觸,為讀者提供了存在主義者的眾多有趣細節,刷新你對哲學家的刻板認識。
★多家媒體“年度好書”,信息量“真大”本書通過綜合哲學、傳記、歷史、文化分析、個人思考,成功地把枯燥晦澀的話題,講成了一個輕松好讀的故事,讓內行也可以看熱鬧,外行也可以看懂門道。
★當人們閱讀薩特論自由,波伏娃論壓迫的隱蔽機制,克爾凱郭爾論焦慮,加繆論反叛,海德格爾論技術,或者梅洛-龐蒂論認知科學時,有時會覺得好像是在讀近的新聞。” ——本書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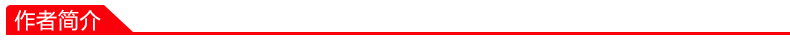
莎拉·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1963年出生于英國的伯恩茅斯,后隨父母在亞洲旅行多年,終在澳大利亞悉尼定居、長大。返回英國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學,攻讀哲學專業,畢業后在倫敦的一家圖書館做了十年圖書管理員。2002年,貝克韋爾辭去工作,開始專職寫作,除本書外,她的作品還包括How to Live(2010)、 English Dane(2005)、 Smart(2002)。她目前生活在倫敦,并在倫敦城市大學和開放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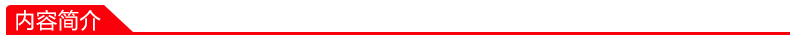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喝杏子雞尾酒。其中一個叫雷蒙·阿隆的年輕哲學家,正在向同為哲學家的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贊一種他在德國發現的新鮮哲學——現象學。“你看,”他說,“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后從中研究出哲學來!”就這樣,20世紀影響guang泛也shen遠的哲學運動發端了。受到啟發的薩特,將現象學與他那種法式的人文主義情感結合在一起,創立了一門全新的哲學思想——現代存在主義。在本書中,英國作家莎拉·貝克韋爾將歷史、傳記與哲學結合在一起,以史詩般恢弘的視角,激情地講述了一個充滿了斗爭、愛情、反抗與背叛的存在主義故事,深入探討了在今天這個紛爭不斷、技術驅動的世界里,當我們每個人再次面對有關jue對自由、全球責任與人類真實性的問題時,曾經也受過它們困擾的存在主義者能告訴我們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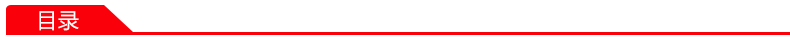
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義!
第二章 回到事物本身
第三章 來自梅斯基爾希的魔法師
第四章 常人,呼喚
第五章 嚼碎開花的扁桃樹
第六章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
第七章 占領,解放
第八章 破壞
第九章 生平考述
第十章 跳舞的哲學家
第十一章 像這樣交叉
第十二章 在處境困難的人眼中
第十三章 一旦品嘗了現象學
第十四章 無法估量的繁盛
出場人物表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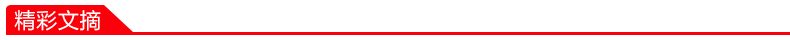
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義!
在本章中,三個人喝著杏子雞尾酒,很多人徹夜長談自由,而更多的人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我們還想弄明白存在主義到底是什么。
有人說,存在主義不太像哲學,倒是更像一種情緒,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傷痛小說家那兒,進而可以追溯到懼怕空間之寂靜的布萊茲·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探索靈魂的圣奧古斯丁,追溯到《舊約》里乏味的《傳道書》,以及那個膽敢質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戲,但終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約伯。簡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個曾對任何事感到過不滿、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將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時間jig確到1932年與1933年之交的某一時刻,其時,三個年輕的哲學家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喝著店里的招牌特飲杏子雞尾酒。
后來詳細講述了整個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時25歲左右的她,喜歡透過優雅面紗下的雙眼近距離地觀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讓-保羅·薩特在一起。薩特時年27歲,佝僂著背,嘴唇像鯰魚一樣下翻,面頰凹陷,耳朵突出,雙眼望著不同的方向,因為他幾乎失明的右眼嚴重散光,時常會向外游離。與他交談時,你一不留神就會覺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著自己注視他的左眼,就會發現一個溫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著你:這個男人對你告訴他的每一件事,感興趣。
薩特和波伏娃的興趣這時上來了,因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訴他倆。這個人是薩特在校時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研究生同學,溫文爾雅的雷蒙·阿隆。和他們倆一樣,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過,薩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國教書——薩特在勒阿弗爾,波伏娃在魯昂——而阿隆卻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訴兩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國發現了一門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個單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皆是冗長而雅致,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揚格詩句。
阿隆也許講了些類似這樣的話:傳統的哲學家常常從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論出發,但是德國的現象學家,卻直接研究起了他們時刻正在經歷的生活。他們把自柏拉圖起就維系哲學發展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諸如“事物是否真實”或者“我們如何確定地知道某事”一類的謎團,擱置在一邊,然后指出,任何問出這些問題的哲學家,本身就已經被拋入了一個充滿事物的世界——或者說,少是一個充滿事物外觀,也就是“現象”(phenomena,出自希臘語,意為“出現的事物”)的世界。所以,為什么不忽略其他,專注于和現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謎團不必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暫時先用括號括起來,好讓哲學家去處理那些更為實際的問題。
現象學家中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提出了一個振奮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to things mselves)!”意思是別在事物不斷累加的詮釋上浪費時間了,尤其是別浪費時間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實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觀察把自己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東西”,且不管“這個東西”可能是什么,然后盡可能jing確地把它描述出來。另一個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補充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縱觀歷史,所有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了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去問那個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你自己意味著什么?海德格爾堅稱,要是你不問這些,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薦現象學方法:無須理會智識的雜亂,只要關注事物,讓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對薩特說:“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這是自學生時代起阿隆對薩特的昵稱——“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后從中研究出哲學來!”
波伏娃寫道,薩特聽到這話后,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張,仿佛是在暗示他倆從未聽說過現象學,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試著讀過一些海德格爾。1931年,海德格爾的演講《形而上學是什么?》(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就曾與薩特早期的一篇論文一起出現在某期《道岔》(Bifur)雜志里。但是,波伏娃寫道,“因為我們一個字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現象學有什么好。”但現在,他們注意到它的好了:這是一種把哲學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起來研究哲學的方式。
他們早已準備好迎接哲學的新開端了。在中學和大學,薩特、波伏娃和阿隆受夠了刻板的法國哲學課程,有關知識的問題以及沒完沒了地重新詮釋康德著作支配了。知識論的問題互相交疊在一起,就像萬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轉后,總是又回到原點: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這種思考費勁而又無用,盡管這三位學生在考試中獲得了高分,但不滿于此,尤以薩特為甚。畢業后,他透露說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新的“破壞性的哲學”,但是對這種哲學會采取什么形式卻又含糊其詞——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當時才剛發展出一種朦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來,現在已經有人早他一步到達了目的地。如果說薩特聽到了阿隆有關現象學的消息后面色發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來自惱怒,一半源于興奮。
反正,薩特從沒忘記那一刻,在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訪中,他評論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現在,終于出現了一種真正的哲學。按照波伏娃的說法,他沖到近的書店,然后說:“給我這里每一本論現象學的書,現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書,胡塞爾的學生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寫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 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維納斯這本書還是未裁開的毛邊本,但薩特等不及拿裁紙刀,直接用手撕開書頁,邊走邊讀。那一刻的他可能變成了濟慈,那個初讀查普曼翻譯的荷馬作品時的濟慈:
那時我覺得仿佛某位觀象家,
當一顆新行星游入他的視野;
或如堅毅的科爾特斯用鷹之眼
凝視著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懷抱一份狂熱的猜測彼此相望——
沉默,在達利安山巔。
薩特沒有鷹的眼睛,也從不善于沉默,但無疑他心里滿是猜測。看到了薩特的熱情后,阿隆建議他在當年秋天時來柏林的法國研究所學習,就像他自己那樣。薩特可以去學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版論著,并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隨著納粹剛剛掌權,1933年并不是搬去德國的好年份。但對于想改變生活方向的薩特來講,卻正是好時候。他厭倦了教書,厭倦了在大學所學的,厭倦了尚未成為自己從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這一現狀。如果要寫他想寫的東西——小說、散文,——他知道首先必須去冒險。他曾想象去君士坦丁堡跟碼頭工人一起勞動,去阿托斯山同僧侶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隨賤民一起躲藏,去紐芬蘭島的海岸和漁民一起抵抗風暴。不過,眼下不在勒阿弗爾教學生,也可以稱得上是冒險了。
薩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過后,他抵達柏林,開始學習。年末返回法國的時候,他帶回了一種融合之后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著更早之前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以及其他思想,又裝點了一味獨特的法國調料——他自己的文學感染力。他以一種現象學創立者未曾想見的但卻更讓人興奮和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創建了一種兼具影響和巴黎風味的新哲學:現代存在主義。
薩特哲學創造的之處在于,他的確把現象學轉化為了一種杏子雞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學,但同時,也是期望、倦怠、憂慮、興奮的哲學,是山間的漫步,是對深愛之人的激情,是來自不喜歡之人的厭惡,是巴黎花園,是勒阿弗爾深秋時的大海,是坐在塞得過滿的坐墊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時乳房往身體里陷的樣子,是拳擊比賽、電影、爵士樂或者瞥見兩個陌生人在路燈下見面時的那種刺激。他在眩暈、窺視、羞恥、虐待、革命、音樂和做愛中——大量地做愛——創造出了一門哲學。
與此前用謹慎的主張和論點來寫作的哲學家不同,薩特會像小說家一樣寫作——用不著驚訝,因為他自己就是小說家。在他的小說、短篇故事和劇本以及哲學論著里,他寫下了關于世界的身體感受和人類生活的結構與情緒。不過,他寫作中重要的內容,是一個宏大的主題:獲得自由意味著什么。
自由,在薩特看來,位于人類所有經驗的中心,正是這一點,才把人類與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其他事物只能在某處待著,聽憑擺布。薩特相信,就連人之外的動物,大多數時候也只是在聽從塑造了它們那個物種的本能和習性行事。但作為一個人,我根本沒有預先被決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過我選擇去做什么來創造。當然,我可能會被我的生物性影響,或者被我所處的文化和個人背景等方面影響,但這些并不能合成一張用來制造我的完整藍圖。我總是先我自己一步,邊前行,邊構筑自身。
薩特把這個原則變成了一句三個單詞的口號——“存在先于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在他看來,這個信條便足以概括存在主義。不過,它雖有簡明扼要之優,可也有不易理解之劣。大概來講,它的意思就是,發現自己被拋入世界中后,我會持續創造我自己的定義(或本性,或本質),但其他客體或生命形式卻不會這樣。你可能認為你可以用一些標簽定義我,但你錯了,因為我始終會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斷地通過行動創造自身,這一點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人類境遇之中,以于在薩特看來,它本身就是人類境遇,從有縷意識那一刻開始,直到死亡將其抹去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這是一個令人沉醉的想法。薩特將其完善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后幾年中——更是因此成了明星人物。他以的身份受到款待與奉承,接受采訪與拍照,受委托撰寫文章和序言,受邀進入各種委員會,發表廣播講話。雖然人們常常請他就他并不專精的各種話題發表意見,但他從來能說得頭頭是道。同樣,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寫小說、新聞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雖然貫穿其中的哲學思想,通常很接近薩特自己的哲學,不過,她的哲學基本上是她獨立形成的,且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他們兩人一起參加巡回演講與售書,有時候參加討論會時,還會被安排在中間,坐在像王座一樣的椅子上——這才符合他們的身份:存在主義的國王與王后。
薩特頭一回意識到他已成為名人,是1945年10月28日在巴黎中央大廳的“現在俱樂部”發表公共演講時。他和組織者低估了過來聽他演講的人數。售票處遭到圍攻,許多人因為他們沒法靠近售票臺,干脆免費進到了里面。在爭搶中,椅子遭到了損壞,有幾位聽眾還在反常的炎熱天氣里暈倒了。或者如一位《時代》雜志的作者給圖片加的注解所說的:“哲學家薩特。女人被迷暈。”
此次演講獲得了的成功。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薩特,站在人群中想必不易被看到,但他振奮人心地闡釋了自己的思想,后來又以此寫了一本書,即《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英譯本名為《存在主義與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演講和書中的高潮處,是一件在剛剛經歷過納粹占領和解放的受眾聽來可能非常熟悉的逸事,而這個故事,也典型地概括了他這種哲學的沖擊力與吸引力。
薩特講到,納粹占領期間的一天,他以前的一個學生來找他指點迷津。1940年,也就是法國仍然在抵抗納粹時,這個年輕人的哥哥在戰斗中遇難了;之后,他父親叛國投敵,還拋棄了妻子。于是,這個年輕人成了他母親wei一的陪伴與支撐。不過,他真正想做的,是偷偷越過邊境線,經西班牙去往英格蘭,加入流亡中的自由法國軍隊,反抗納粹——他想去浴血奮戰一場,有機會來為兄弟復仇,來反抗父親,以及幫助解放他的祖國。可問題是,在獲取食物甚為艱難之時,這樣做會把他母親置于無依無靠的危險境地,也可能會讓德國人找她的麻煩。那么:他應該做對他母親來說正確的事,讓她獨享明顯的益處,還是應該冒險去參加戰斗,做對大多數人有益的事?
哲學家們在解答這類倫理難題時,仍然會爭論不休。薩特的難題在程度上與一個的“電車難題”思維實驗有共通之處:你看見一輛行駛中的火車或電車,正沿著鐵軌沖向不遠處被綁住的五個人——如果你什么不做,這五個人就會死。你注意到,如果扳動一根操縱桿,就可以讓火車變道側軌,但是如果你這么做了,就會殺死一個被綁在側軌上的人;而你不這么做的話,那個人就是安全的。因此,你是愿意犧牲一人,還是什么不做,聽憑五個人死去?(在另一個版本,即所謂的“胖子”難題中,你只能從附近的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扔到鐵軌上,來使火車脫軌。這一次,你要親手去碰你打算殺掉的人身上,因而就為你帶來一個更直接也更難解的窘境。)
薩特的學生要做的抉擇,可以被視為類似“電車難題”的抉擇,但這里的情況更為復雜,因為事實是,他既不確定自己的英國之行是否真的能幫到任何人,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嚴重傷害她。
不過,薩特無意用哲學家——更別提那些所謂的“電車難題專家”了——那種傳統的倫理學推演方式來進行論證。他領著他的聽眾,從更個人的角度思考了這個問題。面臨這樣一個選擇時,感覺如何?一個困惑不解的年輕人,究竟該如何去著手處理這樣一個有關如何行動的決定?誰能幫他,怎么幫?后面這部分,薩特從檢視“誰不能幫他”的角度,進行了探討。來找薩特之前,這位學生曾想過向有聲望的道德求教。他考慮去找神父——但神父有時候正是通敵者本人,而且他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只會告訴他要愛鄰人、要對他人行善事,但卻沒有說清楚“他人”是誰——母親還是法國。接著,他想求助在學校里學過的那些哲學家,按理說,他們應該是智慧的源泉。但哲學家太抽象了:他覺得他們對自己的處境無從置喙。然后,他又試著去聆聽內心的聲音:也許在內心深處,他會找到答案。然而并沒有:在他的靈魂里,這個學生只聽見一堆七嘴八舌的聲音(比如,我必須留下,我必須要走,我必須做勇敢的事,我必須當個好兒子,我想行動,但我害怕,我不想死,我不得不離開。我會成為一個比爸爸更棒的人!我真的愛我的國家嗎?難道我是裝的?),被這些嘈雜之聲包圍,他甚連自己信不過了。走投無路的年輕人,終想到了他以前的老師薩特,覺得自己少不會從薩特那兒問得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不出所料,薩特聽了他的問題后,簡單地說:“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選擇吧——也就是說,去創造(invent)。”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天賜的奇跡,他說。沒有哪個古老的能夠解除你身負的自由重擔。你盡可以小心翼翼地去權衡各種道德與實際的考慮,但說到底,你得冒險一試,去做點兒什么,而這個什么是什么,由你決定。
薩特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學生是否這覺得有幫助,或是他后決定怎么做。我們甚不知道他是否真實存在,還是幾個年輕朋友的綜合體,抑或是的虛構。薩特希望讀者明白的點是,即使他們的困境沒有那個學生那么,他們每一個人也跟他一樣自由。他要告訴我們的是,也許你認為自己受著道德規范的指引,或者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乃是源于你的心理狀態或過往經歷,或是因為你周圍發生的那些事。這些因素確實會有影響,但把它們全加在一起,也僅僅相當于你必須要做出行動的那個“境遇”。而就算這種境遇難以忍受——也許你正面臨處決,或是被囚禁在蓋世太保的監獄里,或是即將墜落懸崖——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動上決定如何去看待它。從你現在所處的地方開始,你進行選擇。而在選擇中,你便選擇了你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如果這聽起來很難很嚇人,那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如此。薩特并不否認不斷做決定的需要會帶來持續的焦慮。他反而通過指出你做什么真的關重要而強化了這種焦慮。你應當做出選擇,就仿佛代表全人類一樣,擔起人類如何行事的責任重擔。如果你為了逃避責任,便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是環境或者什么糟糕建議的受害者,那你便沒有達到人類生命的要求,而是選擇了一種虛假的存在,脫離了你自己的“真實性”。
但伴隨這可怕一面而來的,還有一個美好的前景:薩特的存在主義暗示的是,只要你一直努力,那就有可能獲得真實與自由。這有多令人激動,也就有多令人懼怕,而且二者的原因還一樣。正如薩特在演講結束后不久的一次采訪中總結的那樣:
沒有任何劃定的道路來引導人去救贖自己;他必須不斷創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創造道路,他便擁有了自由與責任,失去了推脫的借口,而所有希望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思想,在早已確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遭到戰爭破壞的1945年,它更是一個誘人的想法。在法國和其他地方,許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忘掉剛剛過去的日子。以及其中的道德妥協與恐怖,來專注于新的開始。但尋求新的開始,還有更深層次的理由。薩特的聽眾聽到他傳遞的信息時,正值歐洲滿目瘡痍,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消息開始暴露出來,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摧毀之際。戰爭使人們意識到了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人類同胞,有能力偏離文明的規范;怪不得“存在著一種固定不變的人類本性”這一觀念聽起來是那么可疑。無論要在舊世界的廢墟之上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世界,實現它所需要的可靠指導,無法從政治家、宗教、甚是哲學家——在遙遠而又抽象世界里的那種舊式哲學家——這類來源那里獲得了。但現在,一種新式哲學家來了,他們已經準備要大展身手,而且能勝任這項任務。
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薩特提出的大問題是:鑒于我們是自由的,那么在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用好我們的自由?在寫于廣島剛剛被轟炸之后,并在1945年10月(演講的當月)發表的文章《戰爭的終結》( End of War)中,他讓讀者來決定他們想要什么樣的世界,然后使之變成現實。從現在開始,他寫道,我們必須一直要銘記在心的一點是,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毀滅自己以及我們的所有歷史,甚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只有我們的自由選擇能夠阻止我們。如果我們想要活下去,那么我們就必須決定活下去。就這樣,他為人類這個剛剛把自己嚇了個半死,現在終于準備好長大成人、負起責任的物種,提供了一門量身定做的哲學。

活潑、精辟——以全新的目光,令人振奮地審視了那些復雜的頭腦與他們所處的du特時代。
——《科克斯評論》(星級評論)
《存在主義咖啡館》令人耳目一新地回顧了那些曾經陳舊的思想及其興起的環境……全書充滿了各種讓人驚喜的小細節。
——《紐約時報》
《存在主義咖啡館》將傳記、哲學、歷史、文化分析與個人思考雜糅在一起,讀起來饒有趣味。
——《獨立報》
精彩……縝密、清晰——強烈推薦給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
——《圖書館雜志》(星級評論)
年度圖書《存在主義咖啡館》,帶領讀者踏上了一段燦爛多姿、引人共鳴的旅程,回顧了二十世紀wei大的哲學運動之一……對于我們這個人人只關心自我的時代,這本優雅的作品有話要說。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1324171289

........
1324171289

........

1324171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