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世間》(三卷本)是作家梁曉聲歷經數年創作完成的長篇小說,全書一百一十五萬字,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品以北方省會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寫到改革開放后的,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描寫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藝術而雄辯地展現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努力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步,堪稱一部“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作者感同身受,滿懷深情,立足底層,直指人心,于人間煙火處彰顯道義和擔當,在悲歡離合中抒寫情懷和熱望。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一部長篇小說佳作,更是梁曉聲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新的高峰。
梁曉聲長篇小說《人世間》,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于2017年11月正式出版發行,為中國作家協會2017年度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2019年,《人世間》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0年,榮獲中華出版物獎;2021年,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22年1月28日,由《人世間》改編的58集同名電視劇在央視綜合頻道黃金時間播出,成為開年大劇。
918104038

基本信息
......
918104038

......
918104038

《人世間》(三卷本)是作家梁曉聲飽含深情的鴻篇巨著,展現了作家豐厚的生活積累和健旺的創作活力,標志著梁曉聲現實主義小說創作的新高度。《人世間》以北方某省會城市一個平民區——共樂區為背景,刻畫了從這里走出的十幾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巨變。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至改革開放后的,他們有的通過讀書奮斗改變命運成為社會精英,更多的則像父輩那樣努力打拼辛勞謀生。人物的性格命運各有不同,善良正直、自尊自強、勤勞堅忍、互助相幫的人性幽微之光卻永遠閃耀,夢想的力量蕩氣回腸。這是一部關于磨難、奮斗、擔當和友情的小說,平民視角,悲憫情懷,縱橫交錯的復式結構,通過一個個可親可感的人物全景展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讓小說具有了社會生活的史詩品格。
918104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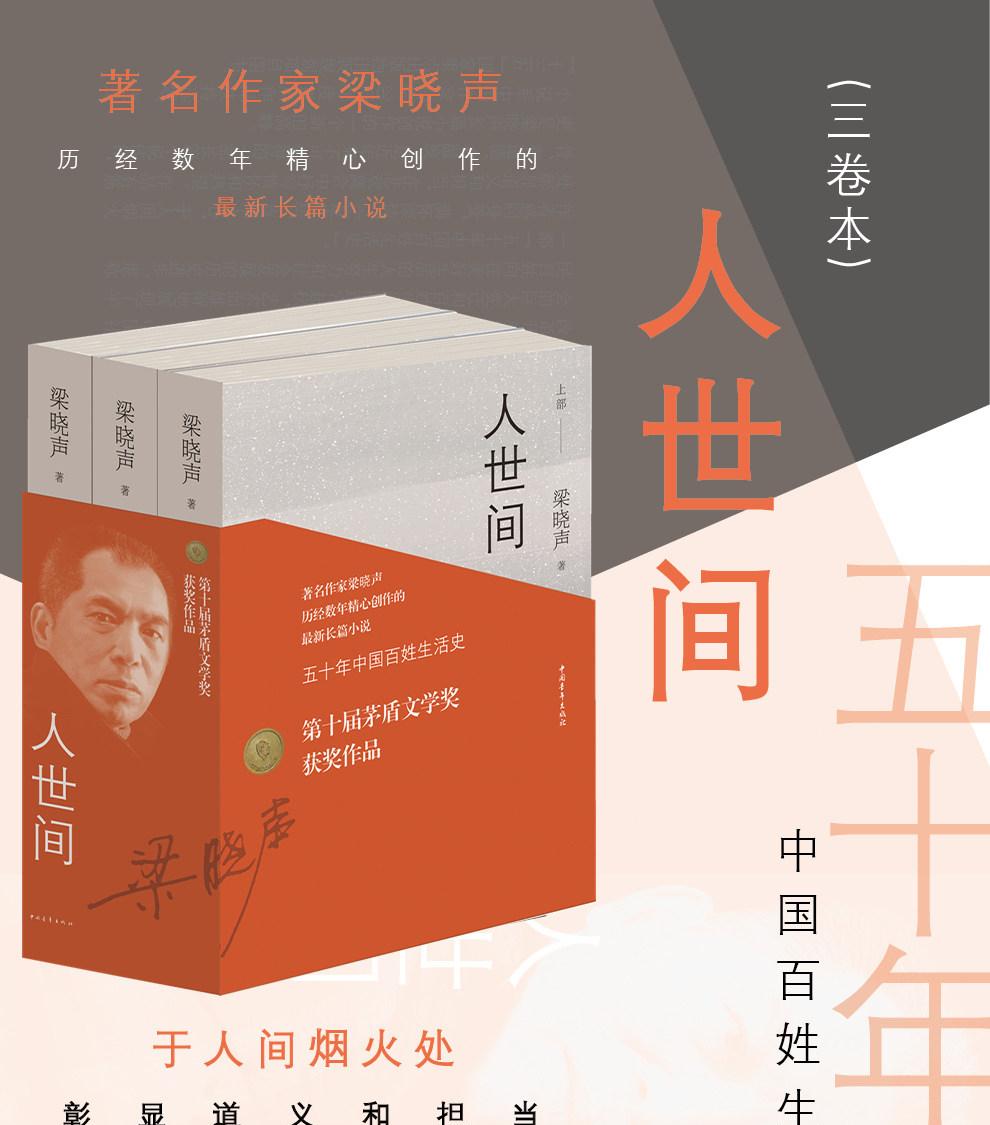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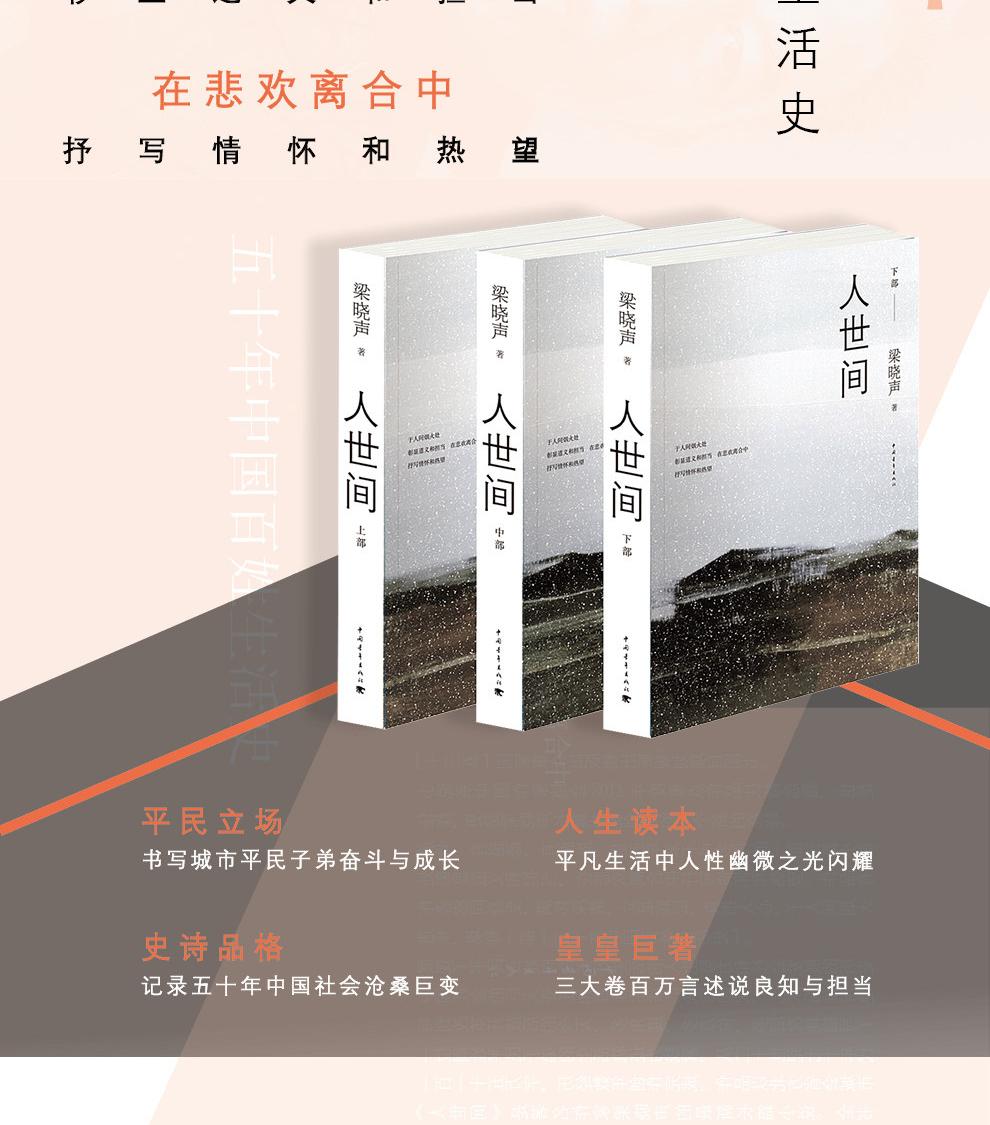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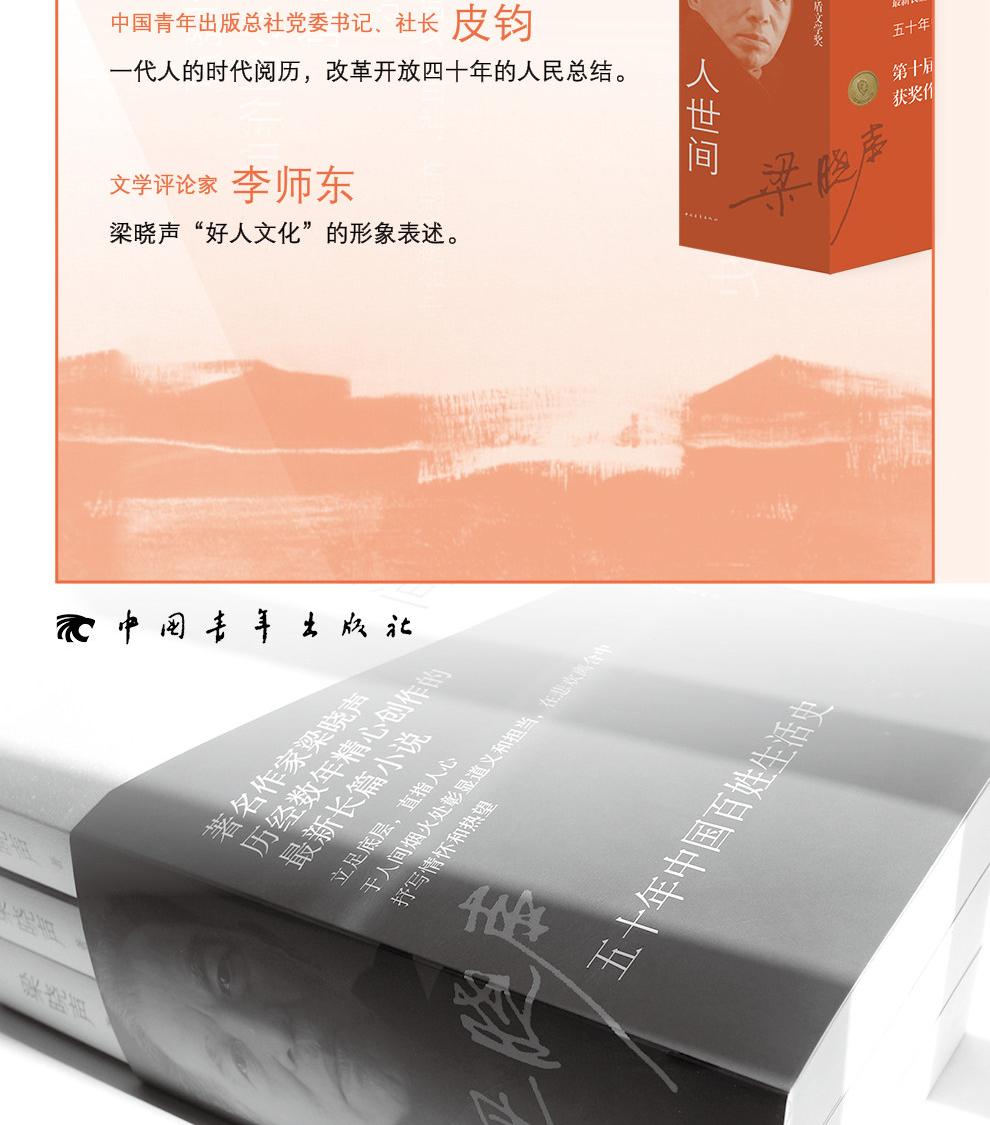
《人世間》節選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親周志剛六十六歲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葉歸根,終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領導們對他這位“大三線”的老建筑工人始終厚愛,有意讓他的工齡延長了兩年,這樣他的工齡就可以達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領元工資。他對此心存很大的感激——盡管受到格外關照,每月也只不過五十二元退休工資。在當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資的人,比許多在職人員的工資還高,很被人羨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個家為端點,向中國那些偏遠的、經濟落后、崇山峻嶺的省份“發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間——A 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發射臺。現在,這一顆“老衛星”耗盡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僅有標志意義了。
常常有人問他這個走南闖北過的人,哪個省份留給他的印象好?他總說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兒去。
他對A市表現出了別人難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頭一個月里,他整天騎輛舊自行車到處逛,把全市的邊邊角角以及四周郊區都逛遍了。他逛得特過癮,體會卻只是兩句話:“哪兒都沒變,哪兒都熟悉。”
他對更加臟亂差的光字片一點兒也不嫌棄,因為見過太多比光字片還要臟亂差的情形。同樣的情形,是當年許多農村和城市的常態。四年里,他這位從“大三線”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當成了“小三線”,把自己家所在那條被違章建筑搞成了鋸齒狀的小街當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讓自己的家看上去還有點兒家樣,理所當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點工程——他似乎要獨自承擔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們經常見到他在抹墻,既抹自家的墻,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墻。他抹墻似乎有癮,四年抹薄了幾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選舉先進居民,他毫無爭議地當選了,區委副書記親自獎給他一把系著紅綢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釘了個釘掛在墻上。他依然是個重視榮譽的人。
他的工具不僅是抹板,還有鐵锨。人們也常見他修路,鏟鏟這兒的高,墊墊那兒的低,填填某處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門前的地方。
見到他那么做的人有過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紀的,常常勸他,“拉倒吧!一條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場雨又稀里嘩啦踏爛了。” 他卻說:“弄弄總歸好點兒,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或說:“我往土里摻了爐灰,再下雨不會那么泥濘不堪了。”
四年一晃過去,周志剛更老了。漢字的微妙之處是別國文字沒法比的,只有中國才有“一字師”的說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雖屬民間口頭語,但把那種如變臉般快的無奈感傳達得淋漓盡致。周志剛完全禿頂了,腦殼左右稀疏的頭發全白了。他漸漸蓄起了一尺來長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許灰色,估計繼續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多了。他的腿腳已不靈活,有點兒步履蹣跚,渾身經常這里痛那里酸的。當年在“大三線”工地上對體能的不遺余力的透支,開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別人已經稱他老爺子了,而即使別人不那么稱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識到 自己確實老了。
不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街坊家臨街墻面的義務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墻需幾道工序,先得備下黃泥,還得有足夠的麥秸或谷秸往泥里摻。和好一堆抹墻的泥很需要力氣,他和不動了。黃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黃泥的地方越來越少,那種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現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砸壘的黃泥小屋。當那些小屋住進了人家,如果誰還去周邊挖取黃泥,常常引發嚴重沖突。那些人家會形成一種占山為王的領地意識,攻守同盟,態度兇悍,讓企圖分享公共資源者望黃泥而卻步。
周志剛是潔身自愛的人,當然避免自取其辱。缺少了黃泥,不論他對自家房屋的維修,還是對他們那條臟街所進行的面子工程,都只好停頓下來。畢竟他只是一個老邁的改良者,也只有點兒人生余力做改良者。倘要徹底改造自己家及那條臟街的面貌,需動用推土機和鏟車,需有充足的建材,還需有一支建筑隊——而單匹馬的他只有一把抹板,街坊們心勁兒又不齊。對他們而言,維修自家房屋是分內之事,至于那條臟街已經那樣了,可以怎樣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慮范圍。他們認為那純屬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覺得有失面子,他們則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么臟亂差的地方的人家還有面子值得在乎嗎?還講得起面子嗎?講面子起碼也得有黃泥呀,連黃泥都稀缺了,就只得讓面子見鬼去了。墻皮掉得太不成樣子了,才趁夜到這里那里去偷黃泥。倘誰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后挑著水桶走往與水站相反的方向,那么準是到什么地方偷黃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為了掩人耳目,街坊們對此心照不宣。偷黃泥往往引發人身傷害事件,但由于是剛性需求,也就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周志剛斷不會做那種勾當。他連自家墻上掉下的墻皮也寶貴地留存起來,積少成多,以備用時。他不敢放在門外,怕被偷,專門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節假日,兒女們回來看望他和老伴時,他嘴里常常會忽然蹦出一句話:“你們誰知道哪兒有黃泥嗎?”
兒女們便都裝聾作啞。
他是在兒女面前自尊心極強的父親,不會問第二次的,總用自言自語緩解自己的擔憂:“這個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個家了。”
他們老兩口和外孫女馮玥玥住在那個家里。
918104038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祖籍山東榮成,1949年生于哈爾濱市,當代作家、學者。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輪》《知青》等作品數十部,多部作品被譯介到海外。
918104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