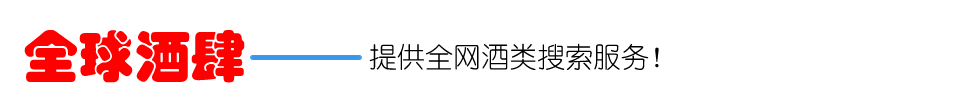......


基本信息
《瑪麗》
《防守》
《眼睛》
《絕望》
《斬首之邀》

......

作為二十世紀公認的杰出小說家和文體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作品對英文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納博科夫精選集I”收錄有《洛麗塔》《微暗的火》《黑暗中的笑聲》《普寧》《說吧,記憶》五部各具特色的作品。
“納博科夫精選集II”精選五部納博科夫代表作,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文字煉金術士的成長:處女作《瑪麗》懷念故國與初戀;《防守》以解剖刀般的精準描繪一位瘋狂的象棋天才;《眼睛》用“間諜”題材挑戰小說技法;《絕望》則玩轉“元小說”,主人公頗有后期《洛麗塔》中亨伯特的影子;《斬首之邀》是一部光怪陸離的超現實黑色寓言。透過跨越十年的五部杰作,可以看到年輕的納博科夫如何進行“風格練習”和寫作探索,從早年天然敏銳的感受力和細膩的書寫,到后期對結構和文體的自如掌控,逐漸構建出的小說宇宙。
“納博科夫精選集II”彌補了多年的市場空缺,滿足讀者們的期待。此次邀請新銳設計師擔綱裝幀設計,令人眼前一亮。
“自莎士比亞之后,沒有第二個作家對語言的澆鑄與運用能夠如此靈動、慧黠和創造力十足。”《每日郵報》如是評論。厄普代克盛贊:“想象的偉力再難找到如此活力充沛的代言人。”
爐火純青的小說技法,幽暗跌宕的現世寓言,縈繞一生的記憶回響。歡迎來到納博科夫的小說世界。如果文字能喚起至純的感官享受,那么舍此無它。

《瑪麗》
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遇見或趕上她,在哪個轉彎處,是在這片還是下一片小樹林里。她住在沃斯克列辛斯克,常常在無人的和煦黃昏、在和他完全相同的時候出來散步。加寧從遠處看見了她,心口頓感涼意。她走得很快,穿著藍裙子,雙手插在白襯衫外面的藍嗶嘰夾克衫口袋里。當加寧像陣輕風趕上她時,他看見的只是在她背上起伏的藍色皺褶和像兩只伸開的翅膀般的黑色綢蝴蝶結。當他滑行經過她身旁時,他看也沒有看她的臉,而是裝作一心騎車;盡管就在一分鐘前,他想象著他們見面的情景時,曾發誓要對她微笑,和她打招呼。那時他覺得她一定有著一個不尋常的、響亮的名字,當他從同一個同學處得知她叫瑪麗時,他一點也不覺得驚奇,就好像他事先已經知道了似的——對他來說這個小小的簡單的名字帶上了新的聲音和一層迷人的意義。
“瑪麗,”加寧輕聲說道,“瑪麗。”他深深吸一口氣,屏住呼吸,傾聽著自己心臟的跳動。這時大約是凌晨三點鐘,火車不開,因此房子似乎靜止不動了。椅子上搭著他脫下來的襯衫,在黑暗中現出白色模糊的形狀,兩只袖子伸開著,像一個人在禱告中間突然僵在了那里。
“瑪麗,”加寧又重復了一遍這個名字,努力想在這兩個音節中放進它曾經含有過的全部的動聽的聲音——風聲、電線桿的嗡嗡聲、幸福——還有另一個給這個名字以生命的秘密的聲音。他仰面躺著,傾聽著自己的過去。不久從隔壁房間里闖進了低低的、輕柔的突—突—突—突聲:阿爾費奧洛夫正翹望著星期六的到來呢。
《防守》
“你怎么樣了?病好些了嗎?”—現實生活中的她怎么知道他夢中的情形?“我們生活在一場美夢中,”他對她輕輕說道,“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他四處望望,看見了桌子,看見了坐在桌子旁的客人面孔,還看見了這些面孔在大茶壺上的投影—在大茶壺上映出很特別的樣子。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這么說這里的一切也是夢?這些人也是夢?這……這……”“輕點,輕點,你胡說什么呀?”她著急地低聲說。盧仁卻認為她說得對,不應該這么亂說把夢嚇跑,讓他們坐在那兒吧,讓這些人暫且坐在那兒。可是這個夢最不尋常之處是周圍顯然都是俄國的東西,做夢的人離開那里已經很多年了。夢中的人物都在高高興興地喝茶,操著俄語交談,那只糖碗也和他許多年前用過的糖碗一模一樣,那是一個血色夏日的黃昏,他在陽臺上用小勺從碗里往外舀砂糖。盧仁饒有興趣而且有點喜悅地注意到他重返俄國了。尤其讓他高興的是,這種重返故國的感覺就像某一套象棋著法饒有趣味地重演一遍一樣—這種情況一般是這樣發生的:比如一套僅限于棋局測驗的著法,理論上創立很久之后,突然在實戰棋局中以驚人的相似面目又出現了一次。
然而,這場夢中自始至終都閃現著他真實的象棋生活,有時模糊,有時清晰。最后夢過去了,現實中只是旅館里的夜晚,為象棋思考,為象棋無眠。他已經發明了一套應對圖拉提開局的防守之策,著法兇悍,還在深思熟慮。他毫無睡意,思路清晰,心中排除了一切雜念,知道除了象棋,萬事不過是美夢一場而已。夢中一位美麗的少女,眼睛清澈,露著雙臂,她的形象漸漸模糊,化為烏有,就像月亮散去金色的光暈一般。當與周圍他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接觸時,他的理智之光常常會散去,由此失去了一半的力量。既然周圍的世界已經變成了虛幻的夢境,再不用為它擔驚受怕,他的理智之光便聚集起來,越來越強。真正的生活,象棋生活,有條不紊,層次分明,富有冒險色彩。盧仁頗為自豪地注意到,在象棋生活中,他輕車熟路,駕馭起來多么輕松,凡事都服從他的意志,聽從他的安排。他在這次柏林大賽上弈出的一些棋局被行家們譽為不朽之作。有一局是在接連棄后、棄車、棄馬之后取勝的。另有一局,他把一個兵放在一個要害部位,使它獲得了怪異的強大力量,還不停地發展壯大,就好像在棋盤上最細嫩的地方長了個癤子一般,害得對手吃盡了苦頭。最后還有一局,他走出了貌似荒謬的一步,在周圍觀棋人中引起了一陣竊竊低語。哪知這是他給對手精心設計的圈套,待到對手察覺為時已晚。在這幾盤對局中,在這次令人難忘的大賽上他弈出的其余對局中,他展示了驚人的清晰思路和冷酷無情的邏輯推理。不過圖拉提也表現出色,也是一分接一分地取勝。他大膽的想象讓對手有點像被催眠了一樣迷迷糊糊。他屢屢憑棋運獲勝,可以說他的棋運自出道至今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他與盧仁一戰將決定誰能奪冠。有些人認為盧仁的思路清晰機敏,會打破那位意大利人不可一世的幻想。也有些人預言攻殺凌厲、有餓虎撲食之勢的圖拉提會擊敗謀略深遠的俄國棋手。他們相遇的日子終于到來了。
《眼睛》
我拖著疲沓的腳步一路走回家,煙盒里空空如也,曉風拂面,臉上火辣辣地燒,仿佛我才剛剛擦掉了登場的粉墨一樣,一投足,一邁步,腦袋就跟著痛一下,每當這個時候,我往往從各個方面查看一下自己那一星星小福分,又是驚奇,又是自憐,又感到沮喪和恐懼。對我而言,做愛的只不過是座荒涼的土包,滿目蕭瑟。畢竟,為了過得快樂,一個男人必須時不時地了解幾段完全空白的瞬間。然而,我總是被暴露無遺,總是大睜著眼睛;即便睡著了,我也沒有停止審視自己,對自己的生存一點兒也弄不明白,又越來越著迷于千萬不能停止對自己的認知這樣一種想法,而且對所有單純的人——職員呀,革命者呀,店老板呀——羨慕不已,因為他們全都信心十足、兢兢業業地干著自己不起眼的工作。我可沒有那種外殼;于是在那些可怕的淡藍色清晨,當我的腳跟橐橐地敲擊著踏過這座城市的荒原時,我常常想象著有人瘋了,因為他開始明明白白地感覺到了地球的運動:他就在那里,踉踉蹌蹌,極力要抓住家具站穩身子;要么在一個靠窗的座位上坐下,興奮地露齒一笑,活像在火車上轉身對著你的那個生客那樣笑著,嘴里還說:“火車跑得真快,是吧!”可不一會兒,這么不住點的搖晃搞得他頭暈惡心;他就開始咂只檸檬,嗍塊冰塊,然后平躺到地板上,然而全是白搭。運動沒有止息,司機是瞎子,哪兒也找不到剎車——車速快得受不了啦,他的心都要迸裂出來了。
我好寂寞啊!瑪蒂爾達常忸忸怩怩地問我是不是寫詩;瑪蒂爾達,在樓梯上,或者在門口,總會巧妙地激我去親她,只不過是找機會假惺惺地哆嗦一下,充滿激情地悄悄說一聲“你這小瘋子……”;瑪蒂爾達當然算不了什么。可在柏林,我還認識誰呢?一個援助流亡者的組織的秘書;雇我當家庭教師的那戶人家;魏因施托克先生,一家俄文書店的老板;先前給我租過一間屋子的德國小老太——一張短短的名單。這樣,我整個毫無防衛能力的身心就招惹起了禍端。一天晚上,災禍惹上身了。
《絕望》
瞧,我又要寫那個詞了。鏡子,鏡子。嗯,發生什么事了嗎?鏡子,鏡子,鏡子。不管你重復多少遍—我什么也不怕。一面鏡子。在一面鏡子里瞧自己。當我這么說時,我是在指我的妻子。要是老被打斷,要講下去就很困難了。
順便說一下,她也很迷信。是一個相信觸摸一下木頭可以祈神的人。在行將做出一個決定前,她便會閉緊嘴唇,匆匆忙忙往四周瞧瞧,尋找光裸的沒有刨過的木頭,只找到桌子底下,粗短的手指觸摸上去(在草莓色手指甲周圍有一小圈肉,雖然她涂了指甲油,卻從來沒干凈過;小孩的指甲)—當那祈求幸福的念念有詞還在空中飄蕩時,她飛快地觸摸一下桌肚子。她信夢:夢見你掉了牙,那就意味著你認識的一個人死了;如果牙上還有血,那就意味著死亡的是你的一個親戚。一地的雛菊預示你將見到你的初戀情人。珍珠代表眼淚。夢見自己穿著白衣服坐在桌子的上座是很糟糕的。泥代表錢;貓意味著叛逆;海洋意味著靈魂的不安。她喜歡詳細地、不厭其煩地復述她的夢。啊!我寫到她時,都是用的動詞過去式。讓我將故事像勒褲帶似的勒得緊一點兒吧。
……
我也許懷著由于進一步美化她所愛的男人而產生的一種曖昧的感情,和她妥協,使她的人生和幸福發生了一個可喜的變化,我利用了她對我的信任,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十年間,我跟她說了無數關于我自己、我的過去、我的冒險的經歷的謊話,以至于我自己都不可能把它們統統記住,每每需要求助于參考材料。但她總是遺忘一切。她把傘輪著個兒落在所有我們認識的人家里;她的口紅會出現在簡直不可思議的地方,譬如她表哥的襯衣口袋里;她從晨報上讀到的東西會在晚上這么對我說:“讓我想想,我在什么地方讀到它的,它到底說什么來著?……我只是隱隱約約記得一點兒—哦,幫幫我!”叫她寄封信等于是把信往河里扔,至于能否收到信,全靠河水水流的速度和收信者是否有垂釣的閑暇了。
《斬首之邀》
就像一個瘋子自以為是上帝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會死的。
——德拉朗德《關于影子的演講》
一
依照法律規定,死刑判決是低聲向辛辛納特斯?C宣布的。在場的人全都站了起來,彼此交換著微笑。滿頭白發的法官把嘴湊近他耳旁,喘了口粗氣,宣布完畢,緩緩走開,仿佛舍不得離去。辛辛納特斯隨即被押回要塞。路繞著要塞的石頭山麓蜿蜒而上,到大門底下消失了,就像一條蛇消失在一道裂縫里一般。他很鎮靜,但是在長廊行走時得有人攙扶,因為他步履蹣跚,像個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又像是一個夢見自己行走在水面上的人,一腳踩空時才突生疑問:一直走得好好的,怎么會掉下去呢?獄卒羅迪恩費了好長時間,才把辛辛納特斯囚室的門打開——拿錯了鑰匙——通常都要如此折騰一番。門終于開了。律師已經在里面等著他。律師坐在床上,埋頭深思,身上沒穿燕尾服(忘在審判室的靠背椅上了——那天很熱,一整天都令人沮喪)。囚犯剛被帶進來,他迫不及待立即跳起來。可是辛辛納特斯心情不佳,不想談話。盡管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獨自待在這間囚室里,囚室還有窺孔,就像小船上的一個漏洞——他并不在乎,堅持要求不受打擾,于是他們向他鞠躬后,便離開了。
至此,我們的故事似乎快結束了。我們看小說看得高興的時候,往往會輕輕地摸一摸右手邊尚未讀完的部分,機械地測定是否還剩很多(如果我們的手指頭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厚度,心里總是很高興),可是現在剩下的部分無緣無故地突然變得很薄了:快點看幾分鐘就完了,已經在收尾了——噢,真是糟透了!原來我們覺得有一大堆黑中泛紅的光潔櫻桃,現在突然變成稀稀落落的幾顆:那顆帶傷痕的已經有點爛了,這顆已經枯干,剩下皮包核了(最后一顆必定是又生又硬),噢,真是糟透了!辛辛納特斯脫下絲質外套,穿上晨衣,跺了跺腳,讓它們不再顫抖,開始在囚室里來回踱步。桌上一張干凈的白紙閃著光,白紙上輪廓鮮明地擺著一支削得很漂亮的鉛筆,除辛辛納特斯之外,它和任何人的生命一樣長,六面都閃著烏木的光澤。它是食指的一個文明后裔。辛辛納特斯寫道:“盡管落到這步田地,相對而言,我還活著。畢竟我早有預感,對這種結局早有預感。”羅迪恩站在門外,像個船長似的,透過窺孔嚴肅認真地窺視著。辛辛納特斯覺得后腦勺涼颼颼的。他把自己寫下的文字劃掉,開始輕輕地涂黑;一個尚未成形的構思漸漸有了形狀,卷曲成一個羊角狀。噢,真是糟透了!羅迪恩透過藍色的舷窗凝視著時升時降的地平線。是誰暈船了?是辛辛納特斯。他突然全身冒汗,一切全都變黑,他能感覺到每一根毛發的微小發根的存在。時鐘敲響了——四下或五下——其震動和再震動和回響和一座監獄都很相稱。一只蜘蛛——囚犯的正式朋友——用腳順著一根蛛絲從天花板上爬下來。但是沒有人叩墻,因為偌大的監獄里迄今只關押著辛辛納特斯一個囚犯!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杰出小說家和文體家。
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后,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
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韋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志》《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并引發爭議。
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