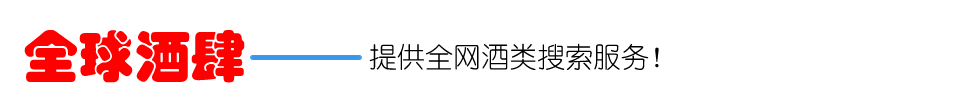一一年三月十日,病中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致信作協書記處:“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事業繁榮昌盛!”
茅盾文獎遂成為中國當代文的*獎項,自一二年起,基本為年一屆。獲獎作品反映了一七七年以后長篇小說創作發展的軌跡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當代長篇小說文庫中的翹楚之作,在讀者中產了廣泛的、持續的影響。
人民文出版社曾于一年起出版“茅盾文獎獲獎書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獲獎作品。二〇〇年,在讀者、作者、作者親屬和有關出版社的建議、推動與大力支持下,我們編輯出版了“茅盾文獎獲獎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為讀者心目中“茅獎”獲獎作品的權威版本。現在,我們又推出不同裝幀的“茅盾文獎獲獎作品全集”,以滿足廣大讀者和圖書愛好者閱讀、收藏的需求。
獲茅盾文獎殊榮的長篇小說層出不窮,“茅盾文獎獲獎作品全集”的規模也將不斷擴大。感謝獲獎作者、作者親屬和有關出版社,讓我們共同努力,為當代長篇小說創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貢獻,為廣大讀者提供更多的作品。
人民文出版社編輯部

基本信息
......

......

《茶人三部曲》*部《南方有嘉木》、第二部《不夜之侯》獲第五屆茅盾文獎,第三部為《筑草為城》。
《茶人三部曲:全3冊》以綠茶之都杭州的忘憂茶莊主人杭齋家族代人起伏跌宕的命運變化為主線,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趙寄客、沈綠愛等各具不同社會意義和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在憂患深重的人道路上堅忍負重、蕩污滌垢、流血犧牲仍掙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氣質和風神,寄寓著中華民族求存、求發展的堅毅精神和酷愛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傾向。茶的青煙、血的蒸氣、心的碰撞、愛的糾纏,在作者清麗柔婉而勁力內斂的筆下交織;世紀風云、杭城史影、茶業興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帶,熔于一爐,顯示了作者在當前尤為難得的嚴謹明達的史識和大規模描寫社會現象的腕力。

當時杭州市面上的樣茶——也就是評茶時的實物依據,大體上分為烘青樣板、大方樣板、黃湯樣板(即建德、分水二本)、青湯樣板(即東陽、義烏、武義等路烘青),吳升均已爛熟于胸。
他的評茶房設在樓上朝南的大屋里,光線柔和,照得一塵不染的地板,進屋得換鞋子。為了避免陽光直射,窗口還裝了黑色遮光板。
屋里又有兩張評茶臺,漆成黑色的那張靠窗口,評干茶;漆成白色的那張放評茶杯碗,評濕茶。
這些,原本都是繼承了茶清的,沒什么新創意,吳升接手后的大膽革新則是立刻叫人刮目相看的兩樁:一是樣茶每袋抓一把減少成三袋抽一把;二是水傭從百分之二三減到只取百分之一點五。
山客水客爭相傳頌,紛紛擁來,吳升看似虧了,實際賺了。同行中人便氣憤,說是破了做意之規,茶漆會館要開會聲討。吳升理都不理:“開會?媽爸個賤胎!開會去呀!你們會開完,老子茶葉老早賣光了!”
茶漆會館競拿這流氓老板沒得辦法,只好去找忘憂茶莊。沈綠愛這頭在做郵包意,顧不過來,便去尋天醉,天醉揮揮手,說:“隨他去,吳升這個好佬,胸脯拍得嘭嘭響,圖個好聽,山客水客也多辛苦,這口飯讓他們吃得爽快一些也好。”
杭天醉沒中有想到,他一進茶行,就有山客朝他吐唾沫星子了。
山客罵著吳升:“你當你是個好東西,騙過了眾人,騙得過我?你和茶清伯比脫頭脫腳了!茶清伯會把一級龍井評成二級?”
吳升一只手擼著嘉喬,一只手拿著一根茶梗,問:“這茶梗哪里來的?”
“茶梗明明是你放進去的,你要加害于我啊。”
“你叫孩子說,小孩不說謊話。孩子一直在旁邊看著呢。”
……
浙西茶苗在遙遠的南亞次大陸迅速繁殖之際,它的故鄉對它的行蹤幾乎一無所知。上世紀中葉,這個清帝國的富庶省份,正在一場大戰亂之中。
東南一隅的浙江,本來有著性情溫和的歲節和濕潤多情的雨季。縹緲的霧氣在清晨與傍晚繚繞省城杭州的三面峰巒,那里是小葉種灌木茶林長的舒適溫床。
憤怒的拜信上帝教的中國南方的農民們,聚集為太平軍,頭上裹著紅巾,被稱之為長毛,占據了這個茶商云集的集散之地。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春三月三十日,駐扎杭州的太平軍彈盡糧絕,在死守兩年三個月之后,終于在夜半時分,撤出武林門,退向德清。
次日,余杭相繼失守,清軍人城。
馬戛爾尼和長毛都不會對位居杭州城羊壩頭忘憂茶莊的杭老板產實質性的影響。同樣也染上了芙蓉癮的中年男人,繼承了杭氏家族綿延不絕的茶之產業,系有忘憂茶莊一座、忘憂樓府數進。涌金門的忘憂茶樓一幢,昔因抽大煙之故,易手他人。
沉醉在煙氣中的杭老板,與他共讀過同一私塾的郊外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均為樂天知命之人。他們有著自己的存方式,對朝廷和國家都缺乏必要的熱情。官府也罷,長毛也罷,首先不要影響他們發財致富,其次不要影響他們婚喪嫁娶。說實話,長毛對忘 憂茶莊倒也不薄,發給它“店憑”,準它開業經營,茶莊所在地,又是 太平軍劃出的買賣街,長毛也要喝茶的,茶莊意倒也興旺。
至于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經營的幾十畝藕田,夏來都開荷花,秋去都藕節,天道有常,無須過問。
倒是女兒一年年大了,等著嫁到城里去的,是件要事。
恰在那樣一個林秀才女兒待嫁的夜晚,杭老板發現他那失去母親的十歲的獨兒子杭齋,躺在榻席上,點著了山西產的太谷煙燈,并把翡翠嘴的煙槍對了上去。
一股迷香,撲上鼻間。杭老板心里一聲叫苦:不好! 杭、林二家兒女完婚之事被推上首要議事日程。
浙江的茶樹正在加爾各答茁壯成長;太平軍已經退出杭州;新知府薛時雨走馬上任并坐在轎中口占《人杭州城》詩一首。與此同時,杭老板和林秀才兩家終成姻親。
新郎杭齋和新娘林藕初對這樁親事,骨子里都持反對態度。在女方,是因為聽說杭氏父子都抽上了大煙;但沒有婆婆壓制的寬松環境又多少抵消了這一短處。在男方,是因為父親以他吸煙為成親條件,但成親后茶莊將由他掌管,亦使他終于心平氣和。
他們便都偽裝得木訥,按照傳統,由著七親眷們擺布。
與此同時,一隊清兵正在清河坊的街巷里,窮兇極惡地追捕一個負隅頑抗的長毛將士。
長毛身手不凡,臉上蒙塊黑布,露兩只眼睛,身輕如燕,體態矯健,嗖嗖嗖幾下躥上人家的屋檐,在那斜聳的瓦脊上一溜箭跑,瓦片競不碎一塊。市民出來抬頭見著,心里頭叫好,也有把那“好”字從嘴上叫了出來的。屋下清兵便大怒,一個個的也想上房,爬不了半截卻又摔將下來,便更怒,叫喊著追逐來去。
跑過幾道巷子,便聽得到一溜高墻后面,有人吹吹打打,已是濃暮時分。那邊,忘憂樓府中,正在大辦喜事。
從拜天地的廳堂至洞房,要經過露天的一個天井花園。被七大姑大姨撥得頭暈目眩的新郎杭齋,正昏頭昏腦地用大紅綢緞帶子牽著比他大了三歲的新娘子林藕初往洞房走。說時遲,那時快,從天上掉下來一個人,狠狠擦過院中那株大玉蘭花樹,然后一個跟頭,便悶悶地砸在了新娘子身上。新娘子一聲“啊呀”,便踉蹌倒地。
時運,就這樣措手不及,把新娘子林藕初推到人前亮相。
林藕初一個翻身爬起,一把揭掉蓋在頭上的紅頭巾,又把那人一下子托起,旁邊那些人才嗡聲起: “長毛!長毛!從墻那邊翻過來的。”此時,大門口,清兵已沖將進來了。
杭齋湊過來一看,面孔煞白,抬頭**次瞪著新娘子:“怎么辦?” 從此以后,一他都問媳婦“怎么辦”了。
小地主的女兒林藕初,畢竟是在鄉間的風吹日曬中受過鍛煉的,二話不說,拖起那人就往洞房里走。
七手腳拖進洞房床前,新娘子將大紅袍子三兩下脫了就披在他身上,頭上一塊頭巾蓋住,一把將他按在床沿。那人坐不住,搖搖晃晃要倒,新娘子騰地跳上床,拉過一疊被子就頂住他腰。那人又往前倒,新娘子手指新郎:“你,過來!”新郎手足無措:“你是說我?”話音未落,已被一把拖住拉到床沿,與那人并肩坐下,那人立即扎進新郎懷中,新郎連忙一把摟住,看上去兩人便像了一對迫不及待的鴛鴦。
眾人這才驚醒過來,企圖七嘴舌。不知有誰尖叫一聲:“要頭的!”新娘子面孔慘白,涂脂抹粉也沒用,聲色俱厲,喝道:“誰說出去一個字,大家都頭。”立刻把那尖叫者悶了回去。
就在這個時候,清兵進了院子,大家都嚇傻了,也沒人上去照應。那頭兒在院中喊:“人呢,這家說話的主人呢?”

王旭烽,155年出于杭嘉湖平原,12年畢業于杭州大歷史系。現為浙江農林大漢語國際推廣茶文化傳播基地主任,茶文化科帶頭人,教授。著有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愛情西湖》《斜陽溫柔》《飄羽之重》,紀實文作品《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啊》《家國書》《主義之花》,隨筆集《愛茶者說》《走讀西湖》《瑞草之國》《一片葉子》《茶的故事》《旭烽茶話》《走讀浙江》,戲劇劇本有越劇《藏書之家》、昆劇《紅樓夢》、話劇《羨歌》等。作品被翻譯成十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