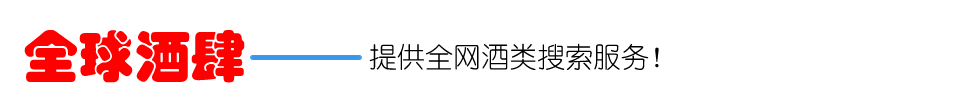蕭紅的寫作生涯,從正式發表作品起,當始于1931年而終于1942年,為期十年左右。本書按寫作及發表時間先后排序,分為上中下三卷。
這套書由學者林賢治先生編注,除蕭紅雖參與署名但實為集體創作的作品外,囊括了她全部作品。林賢治先生對每篇每部作品都附加了注解,對蕭紅創作時的境遇、心境、思想以及文字風格特質做了言簡意賅的概括,對研究者和讀者十分有助益。

基本信息
編輯說明
前言:蕭紅和她的弱勢文學
*輯 哈爾濱—青島(1932-1934)
可紀念的楓葉
偶然想起
靜
栽花
公園
春曲(六首)
八月天
幻覺
棄兒
王阿嫂的死
看風箏
腿上的繃帶
小黑狗
太太與西瓜
兩個青蛙
啞老人
夜風
葉子
廣告副手
中秋節
清晨的馬路上
渺茫中
煩擾的一日
破落之街
離去
出嫁
蹲在洋車上
夏夜
鍍金的學說
生死場
第二輯 上海—東京—北平—上海(1934-1937)
過夜
小六
三個無聊人
索菲亞的愁苦
初冬
歐羅巴旅館
他去追求職業
家庭教師
來客
提籃者
餓
搬家
*末的一塊木柈
黑“列巴”和白鹽
度日
飛雪
他的上唇掛霜了
當鋪
借
買皮帽
廣告員的夢想
新識
“牽牛房”
十元鈔票
同命運的小魚
幾個歡快的日子
女教師
春意掛上了樹梢
小偷、車夫和老頭
公園
夏夜
家庭教師是強盜
冊子
劇團
白面孔
又是冬天
門前的黑影
決意
一個南方的姑娘
生人
又是春天
患病
十三天
拍賣家具
*后的一個星期
訪問
手
馬房之夜
橋
孤獨的生活
紅的果園
家族以外的人
牛車上
王四的故事
長白山的血跡
致黃源
女子裝飾的心理
亞麗
感情的碎片
的憧憬和追求
苦杯(十一首)
沙粒(三十六首)
拜墓詩
兩朋友
天空的點綴
失眠之夜
一粒土泥
致蕭軍
第三輯 武漢—西安—武漢—重慶(1938-1940)
祖父死了的時候
魯迅先生記(一)
魯迅先生記(二)
逝者已矣!
火線外(二章)
一條鐵路底完成
一九二九年底愚昧
《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
記鹿地夫婦
致高原
致胡風
致許廣平
無題
黃河
汾河的圓月
寄東北流亡者
孩子的講演
朦朧的期待
我之讀世界語
逃難
牙粉醫病法
曠野的呼喊
滑竿
林小二
長安寺
放火者
梧桐
花狗
蓮花池
回憶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生活散記
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山下
第四輯 香港(1940-1942)
《大地的女兒》
——史沫特烈作
致白朗
致華崗(六封)
后花園
呼蘭河傳
馬伯樂
北中國
骨架與靈魂
小城三月
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
“九一八”致弟弟書

......

★ 漂泊的人生,悲憫而富于靈性的文字,二十世紀*秀的中國作家之一,蕭紅作品全集
。
★
編者林賢治先生為每篇每部作品作注解。

蕭紅: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里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么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他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地走去。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飯,還喜歡吃油炸的東西喜歡吃硬的東西,就是后來生病的時候,也不大吃牛奶。雞湯端到旁邊用調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那還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帶了外國酸菜和用絞*機絞成的牛*,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后邊的方桌邊包起來。海嬰公子圍著鬧的起勁,一會按成圓餅的面拿去了,他說做了一只船來,送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看他,轉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雞。許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對他竭力避免加以贊美,若一贊美起來,怕他更做的起勁。
客廳后邊沒到黃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涼,知道衣裳不夠了,但為著忙,沒有加衣裳去。等把餃子包完了看看那數目并不多,這才知道許先生我們談話談得太多,誤了工作。許先生怎樣離開家的,怎樣到天津讀書的,在女師大讀書時怎樣做了家庭教師。她去考家庭教師的那一段描寫,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幾十名,她之能夠當選算是難的了。指望對于學費有點補助,冬天來了,北平又冷,那家離學校又遠,每月除了車子錢之外,若傷風感冒還得自己拿出買阿司匹林的錢來,每月薪金十元要從西城跑到東城……
餃子煮好,一上樓梯,就聽到樓上明朗的魯迅先生的笑聲沖下樓梯來,原來有幾個朋友在樓上也正談得熱鬧。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們又做過,又做過荷葉餅,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贊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魯迅還是在桌上舉著筷子問許先生:“我再吃幾個嗎?”
因為魯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飯后必吃“脾自美”藥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魯迅先生正在校對著*的《海上述林》,我一走進臥室去,從那圓轉椅上魯迅先生轉過來了,向著我,還微微站起了一點。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邊說著一邊向我點頭。
剛剛我不是來過了嗎?怎么會好久不見?就是上午我來的那次周先生忘記了,可是我也每天來呀……怎么都忘記了嗎?
周先生轉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來,他是在開著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剛一放晴,我高興極了,就到魯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樓還喘著。魯迅先生說:“來啦!”我說:“來啦!”
我喘著連茶也喝不下。
魯迅先生就問我:
“有什么事嗎?”
我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著,一種對于沖破憂郁心境的嶄然的會心的笑。
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頭發或拉我的衣裳。
為什么他不拉別人呢?據周先生說:“他看你梳著辮子,和他差不多,別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許先生問著海嬰:“你為什么喜歡她呢?不喜歡別人?”
“她有小辮子。”說著就來拉我的頭發。
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
“字不一定要寫得好,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年青人現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這費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這費了工夫不是他的。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還是展讀著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來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濟時,便戴起眼鏡來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時光。
魯迅先生不游公園,住在上海十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么近也沒有進過。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訴周先生,我說公園里的土松軟了,公園里的風多么柔和。周先生答應選個晴好的天氣,選個禮拜日,海嬰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車一直開到兆豐公園,也算是短途旅行。但這只是想著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園給下了定義。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柳樹什么樹的,樹下擺著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土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
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魯迅先生不肯,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轉彎到×××書店走一趟嗎?”
魯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傷風嗎?不圍巾子,風一吹不就傷風了嗎?”
魯迅先生這些個都不習慣,他說:
“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戴不慣。”
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里出來時,兩只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沖著風就向前走,腋下夾著個黑綢子*的包袱,里邊包著書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帶出去,回來必帶回來。出去時帶著給青年們的信,回來又從書店帶來新的信和青年請魯迅先生看的稿子。
魯迅先生抱著*包袱從外邊回來,還提著一把傘,一進門客廳早坐著客人,把傘掛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談起話來。談了很久了,傘上的水滴順著傘桿在地板上已經聚了一堆水。
魯迅先生上樓去拿香煙,抱著*包袱,而那把傘也沒有忘記,順手也帶到樓上去。
魯迅先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他的東西從不隨便散置在任何地方。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口味。許先生想請一個北方廚子,魯迅先生以為開銷太大,請不得的,男傭人,至少要十五元錢的工錢。
所以買米買炭都是許先生下手。我問許先生為什么用兩個女傭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許先生說她們做慣了,海嬰的保姆,海嬰幾個月時就在這里。
正說著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樓梯來了,和我們打了個迎面。
“先生,沒吃茶嗎?”她趕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剛剛下樓時氣喘的聲音還在喉管里咕嚕咕嚕的,她確實年老了。
來了客人,許先生沒有不下廚房的,菜食很豐富,魚,*……都是用大碗裝著,起碼四五碗,多則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筍炒咸菜,再一碗黃花魚。
這菜簡單到極點。
魯迅先生出書的校樣,都用來揩桌,或做什么的。請客人在家里吃飯,吃到半道,魯迅先生回身去拿來校樣給大家分著。客人接到手里一看,這怎么可以?魯迅先生說:
“擦一擦,拿著雞吃,手是膩的。”
到洗澡間去,那邊也擺著校樣紙。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
魯迅先生從下午二三點鐘起就陪客人,陪到五點鐘,陪到六點鐘,客人若在家吃飯,吃完飯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剛剛吃完茶走了,或者還沒走又來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點鐘,十點鐘,常常陪到十二點鐘。從下午三點鐘起,陪到夜里十二點,這么長的時間,魯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斷地吸著煙。
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闔一闔眼睛,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許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邊睡著了。(許先生為什么睡得這樣快?因為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鐘就要來管理家務。)海嬰這時在三樓和保姆一道睡著了。
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臺燈下開始寫文章了。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地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
有時許先生醒了,看著玻璃窗白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么亮了,魯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樣高大。
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著書包,保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保姆總是吩附他說:
“輕一點走,輕一點走。”
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著。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魯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樓的躺椅上,心臟跳動得比平日厲害,臉色微灰了一點。
許先生正相反的,臉色是紅的,眼睛顯得大了,講話的聲音是平靜的,態度并沒有比平日慌張。在樓下一走進客廳來許先生就告訴說:
“周先生病了,氣喘……喘得厲害,在樓上靠在躺椅上。”
魯迅先生呼喘的聲音,不用走到他的旁邊,一進了臥室就聽得到的。鼻子和胡須在扇著,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閉著,差不多不離開手的紙煙,也放棄了。藤椅后邊靠著枕頭,魯迅先生的頭有些向后,兩只手空閑地垂著。眉頭仍和平日一樣沒有聚皺,臉上是平靜的,舒展的,似乎并沒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來了吧?”魯迅先生睜一睜眼睛,“不小心,著了涼呼吸困難……到藏書的房子去翻一翻書……那房子因為沒有人住,特別涼……回來就……”
許先生看周先生說話吃力,趕緊接著說周先生是怎樣氣喘的。
醫生看過了,吃了藥,但喘并未停。下午醫生又來過,剛剛走。
臥室在黃昏里邊一點一點地暗下去,外邊起了一點小風,隔院的樹被風搖著發響。
別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風打著發出自動關開的響聲,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嘩啦嘩啦的響著水聲,一定是晚餐之后洗著杯盤的剩水。晚餐后該散步的散步去了,該會朋友的會友去了,弄堂里來去的稀疏不斷地走著人,而娘姨們還沒有解掉圍裙呢,就依著后門彼此搭訕起來。小孩子們三五一伙前門后門地跑著,弄堂外汽車穿來穿去。
魯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靜地,不動地闔著眼睛,略微灰了的臉色被爐里的火染紅了一點。紙煙聽子蹲在書桌上,蓋著蓋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許先生輕輕地在樓梯上走著,許先生一到樓下去,二樓就只剩了魯迅先生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魯迅先生的胸部有規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魯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體不好,就更沒有時間注意身體,所以要多作,趕快作。當時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為魯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為然,后來讀了魯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魯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時間沒有幾年了,死了是不要緊的,只要留給人類更多,魯迅先生就是這樣。
不久書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擺起來了,果戈里的《死魂靈》,又開始翻譯了。
魯迅先生的身體不大好,容易傷風,傷風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傷風之后總要拖下去一個月或半個月的。
*的,《海上述林》校樣,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魯迅先生不斷地校著,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是十頁八頁的,并不是統統一道地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地被這校樣催索著,魯迅先生竟說:
“看吧,一邊陪著你們談話,一邊看校樣,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
有時客人來了,一邊說著笑話,魯迅先生一邊放下了筆。有的時候也說:“幾個字了……請坐一坐……”
一九三五年冬天許先生說:
“周先生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
有一次魯迅先生到飯館里去請客,來的時候興致很好,還記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鴨子,整個的鴨子用大鋼叉子叉上來時,大家看這鴨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魯迅先生也笑了。
菜剛上滿了,魯迅先生就到躺椅上吸一支煙,并且闔一闔眼睛。一吃完了飯,有的喝了酒的,大家都鬧亂了起來,彼此搶著蘋果,彼此諷刺著玩,說著一些人可笑的話。而魯迅先生這時候,坐在躺椅上,闔著眼睛,很莊嚴地在沉默著,讓拿在手上紙煙的煙絲,裊裊地上升著。
別人以為魯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許先生說,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體是不如從前了,吃過了飯總要閉一閉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從前一向沒有這習慣。”
海嬰每晚臨睡時必向爸爸媽媽說:“明朝會!”
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樓去的樓梯口上喊著:
“爸爸,明朝會!”
魯迅先生那時正病的沉重,喉嚨里邊似乎有痰,那回答的聲音很小,海嬰沒有聽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會!”他等一等,聽不到回答的聲音,他就大聲地連串地喊起來:
“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爸爸,明朝會……”
他的保姆在前邊往樓上拖他,說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夠聽呢,仍舊喊。
這時魯迅先生說“明朝會”,還沒有說出來喉嚨里邊就像有東西在那里堵塞著,聲音無論如何放不大。到后來,魯迅先生掙扎著把頭抬起來才很大聲地說出:
“明朝會,明朝會。”
說完了就咳嗽起來。
許先生被驚動得從樓下跑來了,不住地訓斥著海嬰。
海嬰一邊哭著一邊上樓去了,嘴里嘮叨著:
“爸爸是個聾人哪!”
魯迅先生沒有聽到海嬰的話,還在那里咳嗽著。
從七月以后魯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來了,牛奶,雞湯之類,為了醫生所囑也隔三差五地吃著,人雖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魯迅先生說自己體質的本質是好的,若差一點的,就讓病打倒了。
這一次魯迅先生保持了很長時間,沒有下樓更沒有到外邊去過。
有人來問他這樣那樣的,他說:
“你們自己學著做,若沒有我呢!”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
還有一樣不同的,覺得做事要多做……
魯迅先生以為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為魯迅先生好了。
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過了三個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終日喘著。
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1939年10月

蕭紅 現代作家,本名張廼瑩,筆名蕭紅、悄吟、田娣、玲玲。1911年生于黑龍江省呼蘭府一個地主家庭。為了追求自由和理想,一生輾轉于中國動蕩的土地上。1942年在日軍的空襲和占領下病逝于香港,年僅三十一歲。在她漂泊的生涯中,留下了《生死場》《呼蘭河傳》《馬伯樂》等在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經典作品。她以開闊的悲憫情懷關注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的意義,其文字風格渾然天成,富于靈性,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之一。
編注者:林賢治 詩人,學者。1948年生,廣東陽江人。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曠代的憂傷》《孤獨的異邦人》《火與廢墟》;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自制的海圖》《五四之魂》《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午夜的幽光》《紙上的聲音》《夜聽潮集》;文學史著作《中國新詩五十年》《中國散文五十年》;政治學著作《革命尋思錄》;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沉思與反抗》《林賢治自選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后十年》《漂泊者蕭紅》《巴金:浮沉一百年》;訪談錄《呼喊與耳語之間》等。主編叢書叢刊數十種。